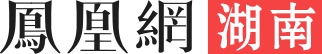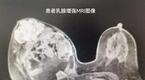长沙之野问字风(文脉长沙)
一
长沙最早的文字就两个字:大禾
冬日阳光温暖。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人,直奔隐没在山野的宁乡沩山乡同庆村罗花组,寻找叫铁磨善尼禅师灵骨塔的石刻。
石刻藏在一个陡坡上。他们正爬得气小喘、脸微红、汗将冒之际,一块鲜为人知的僧尼灵塔碑耸立在众人面前。碑系清代光绪十三年(1887)立,从碑文追溯的铁磨禅师事迹看,文字记载的主人翁是唐代一位不为正史所载的佛家人物。
这发现并不惊天动地,但正是这块石刻文字,留下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续上了长沙山野一段劝人向善的美好记忆。
文字,只有文字,才是最好的文化符号,这块名不见经传的僧尼灵塔石刻碑面世,又一次唤起了人们追寻长沙文字源头的兴趣。
站立山坡,回望沩山,林影依依,似有古刹钟声渺渺而去;远眺沩水,河流汤汤,但见文明的脚步款款而来。就在脚下这块土地,不是出土过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么?那么,谁是长沙第一个接触、认识这些文字的幸运者呢?
1959年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湖南省博物馆几位考古专家在长沙废铜仓库有惊人的收获,蹲守仓库多天的专家们从堆积如山的废铜中,翻拣到了一件商代的人面方鼎,方鼎的内壁,居然还有两个字:“大禾”!
多天的劳累一扫而光,带着兴奋,考古专家追本溯源,最后找到了这件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是在宁乡黄材炭河里叫新屋湾的地方,从鼎的出土地点跨过沩水,就走进了著名的西周古城炭河里。
这是长沙首次在青铜器上发现两个字,也是长沙最早的文字之一!专家们对这两个字的考证甚至惊动了全国的古文字研究大家。字被释读为“大禾”,字体风格与中原同时期的金文完全一样,这两个字的年代,离今天已经有3000多年了。
“大禾”是一个方国,还是一座城池?抑或就是铸造这尊人面方鼎的人名?谁知道咧!但就这区区两个字,足可以让人产生无尽浮想。一横、一撇、一捺,一个“大”字;一撇、一横、一竖,再一撇一捺,一个“禾”字。这两个字无不令人魂牵梦绕,凝神屏气。仔细看,慢慢品,“大禾”两字的背后,该是隐藏怎样撩人的故事?
3000多年前,有字的青铜器,在长沙乃至湖南、长江以南都是不多见的,著名的四川三星堆发现那么多青铜器,很少看到哪件器物上铸造了文字,长沙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文字,背后的故事一定不简单。
3000多年前,被长沙人初识的文字,可不只有这两个,宁乡的乡野不断带给长沙人惊喜。1962年的一天,宁乡黄材栗山张家坳百姓在当地叫水塘湾的地方起土时,挖出一件商代青铜鼎,器上铸有“己冉”二字;1963年的5月,沩水发了一场大水,沩水上游的支流塅溪河上,大水冲来了一件商代兽面纹提梁卣,盖内、器底均铸有“癸冉”二字;1972年2月,同样是在沩水上游叫王家坟山的地方,百姓又发现了一件带有“戈”字铭文的商代青铜提梁卣;1996年,沩水下游望城一个叫高砂脊的地方,从19座墓、约30余件青铜器中,发现了一件铸“酉”字铭文的青铜器。此外,宁乡还发现了一件出土后差点流失、后收藏在益阳博物馆、铸有“冉父乙”三字的商代青铜罍。
要在湖南、尤其是长沙的商周青铜器上发现文字,真不是件容易的事,2003—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炭河里西周古城及周边大搜索,总算找到了7座墓,但居然没发现一件有字的青铜器!据专家们统计,长沙目前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已有好几百件了,但上面铸有文字的青铜器有5件,累积的字数也就是11个。
这11个字,看似有点少,但却是与殷墟甲骨文同一年代流行的文字,更是目前追寻长沙文字之源的珍宝。
这些有字的器物发现前,没有人会相信,3000多年前的长沙,已经开始接触中原的文字了!这些青铜器的铸造者、使用者、拥有者、接触者,不仅是长沙,而且是湖南,乃至长江以南最早的一批识字者。
正是从这11个字开始,文字在长沙传播、在南蛮之地传播、在长江之南传播,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字作为记事、叙事、达义的符号,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与使用,长沙,因为文字的传播,终于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了。
二
先秦战国,“刀笔吏”行走长沙街头
金文,或者说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更多的是显示特权、王权,只属于王家、巫者、贵族等特殊阶层。真正普及的文字,是书写在竹子与木头上的文字,书写了文字的竹子、木头,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简牍”。
商周时期,可能就已经有简牍了,但考古发现的最早简牍,已经到了战国时期,长沙正是中国发现最早最多战国时期简牍的地区。专门制作简牍、抄录文字,在战国时期的长沙当是一门很好的职业。
20世纪40年代,长沙人居家日常所用的燃料是煤炭,制作家用藕煤,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日常事务。为使藕煤充分燃烧后不散架,达到既可充分释放热量又能节约原煤的目的,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煤里掺杂泥土。需求带来了市场,为满足城市居民制作藕煤的需求,长沙城出现了一群以卖土为生的“土夫子”。土夫子在长期的挖土生涯中,发现最好的土就是古墓的填土,时间一长,他们就成了找古墓的高手。随着古董买卖的兴起,卖土的土夫子顺便卖起了古董,做起了盗掘古墓的营生,长沙古墓,因此经历了一场浩劫。简牍在这场浩劫中也难以独善其身,许多珍贵的文字,就这样不可再生了。
尽管如此,长沙仍占据了中国战国简牍出土最重要、最多的位置。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就来到了长沙,开始清理盗墓者毁坏的古墓,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他们在长沙五里牌楚墓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战国楚简。与此同时,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队也开展了相关考古调查,发现了仰天湖、杨家湾两批战国楚简。
长沙楚简,一时轰动全国。
今天能看到的长沙最早、最完整、文字最清晰的楚简,是1953年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发掘的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共有42支,现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院。
这批简加工痕迹清晰可辨,保留了大量制简、写简的信息。每支简长20.2厘米,宽0.9~1.1厘米,文字写在竹黄那一面,竹青是背面,没有被削掉,出土时,竹青清晰可见,俨然散发出“汗青”之味;简的中部右侧,有规律地削出两个小缺口,二者相距8~9厘米,显然是编束成册时韦条打结之处,这又让人未免有“韦编三绝”的遐想。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长沙出现的这批简就是长沙历史。文字是典型的楚字体,字体结构严谨规范、整齐划一,显示出书写者的老到与娴熟。哪怕文字内容是随葬品清册,涉及送礼人、所送物品与数量等,既是一本“人情簿”,又是一卷长沙其时的风俗画。
考古发现的这种随葬品清册,被称着遣策。战国秦汉时期,长沙一带某人去世了,与今天差不多,亲戚朋友必随礼,所送的礼必登记在遣策上。抄写遣策,是一颇有技术或文化含量的“活计”,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职业抄手,史书上所谓“刀笔吏”,最初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抄抄写写的人,并不真的是什么官衔。
刀笔吏之所以称为“刀笔吏”,就是因为刀和笔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工具。抄写简牍文字时,不仅要笔,刀也不可或缺。初步加工的简牍,在刀笔吏们使用时,要随时修整不规整竹片,修整竹片必用到刮刀、削刀。抄写过程中,免不了有抄错的时候,抄错了的话,他们可没有橡皮擦可用,也得用刮刀、削刀解决。刀用多了,刃口会起钝,则需要磨锋利,磨刀的砺石就成了必备品。因此,刮刀、削刀、砺石,与笔同等重要,也是当时文字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品。
刀笔吏使用的刀、笔以及磨刀的砺石,在战国时期的长沙楚墓中有大量发现。
毛笔用竹子和毛制作,竹子和毛发要在墓中保存几千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幸运的是,长沙楚墓居然为今天的人们保存了两支毛笔,其中一支,还十分完整。
1954年6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队员在长沙左家公山清理了一座战国中期楚墓,清理出土文物时,发现一个编制精美的竹箱(笥),打开竹箱,一个十分完整的竹管被仔细地存放在箱子里,打开竹管,里面居然是一支完完整整的毛笔!笔杆长18.5厘米,直径0.4厘米,毫毛长2.5厘米,毫毛为上好兔箭。从毛笔痕迹判断,制作时,先选根大小适合的竹竿,将一端劈成数开,再将精挑细选的兔子箭毫夹在劈开的地方,然后用丝线缠紧,再髹一层漆,漆干后,一支上好毛笔就制成了。这样的毛笔,竹制的笔杆细长,笔毫的锋很尖细。
显然,这支笔是墓主人生前十分珍爱之物,不仅作为随葬品带走,而且精细地包装放置。他是否用这支毛笔写过字?甚至是否就用这支毛笔在社会上行走?这位“左家公山人”如何使用他的毛笔已无从考究,但人们今天能看到的,长沙出土的、战国到汉代的简牍乃至楚国帛书上的文字,字体结构圆转、扁平,笔划尖锐,抄手使用的,应该就是使用这种毛笔。
用于书写的简牍,光有毛笔是不行的。制作竹简,从伐竹、除青到编缀成册,是系统工程,需要作业链条支撑,随着读书重要性的提升、识字者的增多、文化的推广、教育的兴起,简册需求量必定大增,类似现代出版行业一般的简册制作行业就应运而生了。至迟,在战国中期前后的长沙,这样的行业就出现了,正是这一行业的兴起,助推了长沙文字的传播、文化的发展。
考古学提供了有限但也是明确的这方面的信息。长沙迄今发现的战国楚墓中,用铜、铁制作的刮刀、削刀,石头制作的砺石,分别随葬于60多处,这无疑是当年长沙文风鼎盛的缩影。如果稍微把历史的轴线往后拉一拉,1996年,长沙走马楼发现东汉晚期到三国时期的简牍10万余枚、字数多达200多万,其中需要的人力物力,不是一个小数目。若不是专门机构、专门的人去做,又岂可做到?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为战国以来长沙刀笔吏所作的贡献、为长沙的竹书时代,画上了辉煌的惊叹号!
人们往往为历史上的文化大师们倾倒,而抄写、推广、制作大师们作品的那些伐竹木者、除汗青者、修简牍者、抄文字者,正是大师、大家文化高峰上不可或缺的一草一木、一坷一石,春秋大义、诸子雄文正是通过这些草木坷石而流传千古、不断光大。他们的故事,值得后人发掘、书写。
战国之后的长沙,文字与文化的传播者,不仅用留下的简牍演绎着中华文化在长沙的故事,还用丝绸呈现了这个故事中的第一个高潮。
三
楚汉时期,长沙人在丝帛上泼墨挥毫
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大聚合、大裂变、大释能,长沙这个在先秦诸子甚至司马迁的大作中还位列蛮荒之地的地方,也大致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吸收与消化,来自诸子百家、国士君王的高论,不仅通过简牍在这里传播、传诵、传承,一些珍贵篇章,还被珍爱的长沙人抄写到贵比黄金的丝帛上,制成了“精品图书”。
1942年,一件稀世奇珍即战国时期的楚帛书在长沙横空出世。
这件文物的出土地点,原为长沙南郊的子弹库,位于天心阁外东南方向的识字岭与左家公山之间。今天的子弹库,早已被长沙的繁华覆盖了。这件楚帛书上,有翰墨书写的900个字、绘有12幅插画。这件帛书出土30年后的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队用现代考古方法对出土帛书的墓葬进行了重新清理,竟然又发现一件稀世珍品《人物御龙帛画》!这件劫后余生的国宝,主人翁是一位男士,作品在设色、勾线的技巧方面,粗细、刚柔、动静的表现恰到好处,画面还用金粉、白粉进行点缀,显示了绘画者的专业能力与水平。与子弹库帛书、帛画年代差不多、发现于长沙陈家大山的著名的《人物龙凤帛画》,是一件出土于1949年的战国帛画珍品,主人翁是一位女士,作品画面的构图,有上、中、下三层,三层清晰而简练,人物、凤、龙主次分明,尤其是人物婀娜身姿的刻画,将楚时代长沙人的审美情趣进行了生动诠释。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两幅帛画中的人物,刻画的对象,可能就是墓主本人。画师若无一定的功力,是不可能将人物刻画得如此生动传神的。
一件帛书、两幅帛画,是战国时期长沙人用软笔或毛笔创造的绝世名作。帛书是世界上最早且唯一的先秦帛书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术数书、最早的图文并茂图籍;《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发现的采用金、白粉彩点缀画面的最早绘画作品;《人物御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帛画,而且是最早的、以现实人物为对象的肖像画。
穿越时空,一个生动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距今2300年前后的长沙,一群善用毛笔写字、画画的行家里手,或出入豪门、或行走街巷、或走向阡陌,受邀为人写字、画画,在主人的致谢声中,又开始寻找下一个服务的对象……
他们都是谁?今天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们的名字了。据考古专家研究,长沙发现过70多座战国中期前后楚人墓,他们除了有高低不一样的爵位,可能还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角色:“士”。他们有社会地位、能文能武、大多识字,他们的随葬品中,有武器,也多文房用品。
随葬帛书帛画的“子弹库人”,就是其中的一员。经对尸骨鉴定,“子弹库人”身高约1.70米,去世时约40多岁。从墓中帛画对他的刻画看,他是一位身材修长、头戴“切云冠”、腰佩长剑的时髦潇洒的美男子。画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楚国男士的雅致与文气,帛画出土后,郭沫若先生曾欣喜地写《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一诗,诗中有“仿佛三闾再世”之句。这位“子弹库人”是书画爱好者还是书画创造者?已无法下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他能获得他想获得的书画作品,他能找到可书可画的人,那个年代,职业书画师、职业书画行业就已在长沙出现了。
这个行业一经出现,在古代长沙至少连续兴盛了两百年。比这些帛书帛画流行年代晚两百年左右的西汉前期,长沙作为长沙国,第一次在中央王朝有了明确的政区地位。长沙国的存在给长沙带来了安定与繁荣,西汉长沙的书画队伍,延续了战国时期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因为马王堆考古大发现,几近全景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马王堆西汉轪侯利苍家族的墓地有“地下图书馆”的美誉,在这个图书馆里,收藏了大量抄录在丝绸上的先秦经典,字数10多万,内容有45种之多,艺文、诸子、术数、兵书、方技等一应俱全。从这个图书馆能读到原汁原味的先秦诸子大作、能读到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能读到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能读到世界上最早的“测绘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能读到世界上最早的军事部署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还能读到抄写在竹简上的医书、欣赏到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关于天上、人间、地下的大幅空间图像。
有意思的是,这些图书,可不是利苍家一天收藏的,甚至不一定是自己家找人抄录的。考古专家研究发现,其中的很多文献,抄录的时间,与“子弹库人”同时甚至更早!书者的书风、画风,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个人的特点,也许有一天,通过大数据分析,作品书者传承的故事,也可从作品风格、特色的研究中,找到蛛丝马迹!
笔力春秋,文字、书画深刻浸润下的长沙人,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中书写着新的故事。新的故事中,平民与文字的缘分越积越厚。
四
汉唐之时,长沙人用瓷石抒发豪情
尽管金文属于王家、简帛也囿于富贵,但文字的传播,却属于民间、属于乡野。长沙人初识文字的故事发生在乡野,从战国到汉代,那些传播下来的文字与书画故事也发生在乡野,乡野与文字的故事,似乎从来就没有断过。
《后汉书·窦融传》载,公元89年,窦宪领兵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燕然”而还。勒石立碑之风在中原兴起,魏晋以后,北方移民南迁,把这股风吹到了长沙,带来了新一代中原士大夫的追求。宋室南渡以后,来自中原的达官贵人,乱世之中也仍保有一份矜持与文化的骄傲,他们或请辞归隐,或出守左迁,更普遍的,则是“林壑徜徉,自题岁月”,把思想情感赋予山林、刻在石上,留在山石上的文字“其词皆典雅可诵,其书皆飘飘有凌云之志……”这种文人于山间题名刻诗之风,在长沙一经吹起,就一直刮到了今天。
首先吹来长沙的这股风,是碑碣铭刻之风。汉武帝感念贾谊,特别赐长沙国为贾谊勒刻《贾谊纪功碑》,这是明确见于史载的长沙第一块有文字的石头,今天已无缘见其真容了。但自这股风吹来后,文字似乎更加贴近普通民众了,民宅的门框、寺院的石柱、大道的路牌等所在,逐渐出现石刻文字,到了唐代,以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丹的《麓山寺碑》为标志,该碑词章华丽,笔力雄健,刻艺精湛。文采、书法、刻工达到了“三绝”的高度。
因与李邕交怀颇深,当年,杜甫游历岳麓山,见到《麓山寺碑》后不禁一改漂泊之苦,诗兴大发:“飘然斑白身奚适,傍此烟霞茅可诛。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古人遭遇乱世都喜爱退栖隐居,杜甫幸喜来到长沙这片乐土以“养残躯”,或许就是见到《麓山寺碑》这种文字的力量使然。
另一种石刻之风被称为摩崖石刻。长沙的摩崖石刻虽较永州、郴州有差距,但因一块摩崖石刻的出现,使长沙的摩崖石刻达闻天下。这块摩崖石刻就是有“海内第一古刻”之称的《禹碑》。这块被称为碑的的摩崖石刻,摹刻自宋代,从宋代到现在,一直静静地立在岳麓山北峰, 不时有景仰者为其题名、为其建亭保护、为其拓印传播,成为研究《禹碑》最重要、最原汁原味的标本。
长沙的文字,最早出现属于乡野,终于再次回归到了乡野。
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唐代的长沙,在诗歌创作上,也不遑多让,即使贩夫走卒也跃跃欲试,想用文字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于诗文,于是,一个属于长沙、与文字有关的创举,在长沙一个叫石渚的乡野出现了。这就是长沙窑的窑工们在瓷器上写的字、绘的画!窑工们用泥、火、墨、釉淋漓尽致地释放豪迈与情感。今天看到的长沙窑瓷器上的文字,或为诗歌,或为谣谚;或咏爱情,或赋景物;有的还与器皿、绘画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与泥火打交道的人,将源自《诗经》的赋、比、兴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创作的诗篇充满时代气息与长沙乡野情趣。大量的长沙窑瓷诗虽不载于《全唐诗》,但长沙窑瓷诗却是唐代诗歌文化最好的、可触摸到的丰碑。这种瓷器装饰史上的文字表达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是长沙人的独爱,长沙窑既开先河,又达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高度。
有趣的是,长沙窑瓷器上文字书写者的书法水平虽给人很“业余”的感觉,但书法笔势特点却颇像诞生在这里的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父子的风格 。属于石渚、属于长沙、故居离长沙窑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的欧阳询父子,其所创造的书体,书法史上独立成峰,有“大小欧阳体”之称,欧阳父子俩成了后世通行公文“馆阁体”的开山鼻祖,在书坛影响深远。望城书堂山的欧阳家,至今还留有他们练字读书的洗笔池与读书台,长沙窑瓷器上的书写者,是否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年即受到了欧阳父子书风的直接影响、从而刻意效仿呢?
从唐宋开始,文字对于长沙人,不仅像亲人,有时还是“神”一样的存在。离长沙窑大约不到5公里的望城区茶亭镇九峰山村,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惜字塔,这种惜字塔又叫焚字库、焚纸楼、圣迹亭、敬字亭,一看名称,就知道是为了崇文重教而建。这样的塔,塔里烧的不是香烛、纸钱,而是有字的纸张。表面上是告诉大家要“敬惜字纸”,骨子里表达的是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化的崇拜、对先贤的纪念。当一张纸上写了字,就不能随意践踏与遗弃,实在无处可存,就将他们投入塔中烧化,让文字化成一缕青烟去与先贤相会。同样的塔,在长沙远不止这一个,曾经遍布长沙乡野。
是的,当文字散布乡野,并在人们心中成为“神”一样的存在,那么,文明就会像春天的种子,获得蓬勃向上的力量。